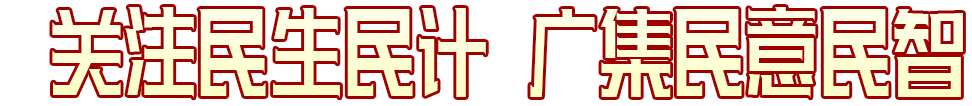中央部门和陕西等地方近期陆续公开了2011年预算,但大多数被认为“不适宜”公开的预算仍隐藏在名为“其他支出”的大类里,其中包括政府人员工资及行政成本等。近年,审计部门在审计中也发现,其他支出频繁使用,金额较大,尤其基层财政更严重。(4月11日《济南日报》)
预算公开是透明财政的必由之路。一片阳光之中,仍有体制化的巨大“黑洞”。有数据说,近年来,一些地方政府的“其他支出”占其财政支出的比重非常高,在30%甚至40%。至于“其他支出”让地方政府爱不释手的原因,无非两者:一是看不到具体支出用途,人大审议时好赖都能通过;二是预算法规定,年度中财政资金在科目间“流转”不需人大审批。
“其他支出”的盖头下,各有各的扮相。但这一项支出之所以令公众浮想联翩,显然不是空穴来风:一方面,几乎各级政府的“其他支出”都是所有二十几个类中数一数二的大支出,比如2011年北京市市级一般预算支出情况表中,按功能分类的支出分类显示,最大的一项为教育支出,达226亿元,而第二大支出项即为“其他支出”146亿元,占总支出的11.6%;另一方面,“其他支出”的历史并不十分光彩,比如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审计局在审计中发现,“其他支出”有扶贫慰问、也有捐款赞助,但更多是支付奖金补助、吃喝招待、参观学习,不好处理、超标的费用都罗列其中。加上“其他支出”中还有“其他”项,层层叠叠,别说民众,审计部门看起来也是眼花缭乱。
公开是常态,秘密是例外。财政支出备受关注,缘于政府部门是非物质生产部门,一丝一缕、一粥一饭,都是纳税人的血汗。财政公开是透明政府的基础,而这个“公开”,当然不是在账目上辟出“其他支出”的秘密通道,技术性地令无妄支出逍遥于社会监督之外。因此,“其他支出”不能成为某些部门拒绝预算公开的最后一个角落,而应该将所有项目呈现在公众的视野下,接受专业审计部门和公众的监督。当然,“其他支出”暗自妖娆,既说明财政公开之难,也说明公开之必要与迫切。
眼下而言,既然公众对这个“其他”的真面目无限好奇,职能部门就有责任和义务为之解惑答疑,揭开“其他”的真相,还公众知情权。毕竟,知情是其他权利的基础,而“不公开”历来是贪腐或寻租的最佳拍档。